早在#eyebrowsonfleek之后的那天,我才12岁,并且第一次为我的眉毛打蜡。我正在佛罗里达州拜访一家人,我亲爱的玛丽姨妈坚持认为是时候驯服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半意大利半亚美尼亚拱门。
我们去了一个水疗中心,当我看到我黄褐色的处女灌木丛时,我可以看到眉毛专家眼中闪烁的光芒。 “你有美丽的眉毛,”她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告诉过我。我有点紧张,但速度很快:蜡壶慢慢晃动,环境音乐播放,两次闪电般的快速条带滑动后,我的眉毛被修剪。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习惯了我的新面貌,考虑到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迪士尼世界,这一点特别困难。我冒着一线红色的主题公园观众的勇敢,微笑着,“噢,亲爱的,没有…”看起来真正令人担忧。在红肿消退后,我终于开始吸收我的新面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女性化的终身假小子。我感觉很好,但是和任何一个青少年一样,在我回到学校并得到中学同学的积极评价之前,我感觉不太好。整个经历是一种祝福和诅咒。
首先,我来看看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或任何年龄,真的)都要珍惜。另一方面,它是我成为普遍的卡拉·迪瓦伊时代过度潮流的牺牲品的门户。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镜子前面,手里拿着镊子,寻找不规则的毛发。当我再也找不到时,我会进一步塑造我的眉毛,痴迷于对称性。这是一个恶性的恶性循环,一直持续到高中和大学。
直到我20岁时,当迪瓦林小姐和她的力量眉毛开始他们的统治时,我认为更大可能更好。我把我的镊子无限期地停下来,当我的眉毛开始长大时,我发现我不仅仅喜欢他们为我的骨骼结构所做的事情,而是我开始感觉更“我”。这是一种奇怪的传染感。事实上,在开始的时候,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嬉皮士的嬉皮士,甚至没有倾向于大多数流浪的头发。编辑们的说明:我已经毕业了很少的修饰和眉毛凝胶。
当我的眉毛恢复昔日浓密的光彩时,我意识到虽然厚厚的拱门有片刻,但它们在历史上一直是强大女性的共同特征。来自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她用浓密的眉毛勾勒出她眼睛的眼睛;对于伊丽莎白泰勒来说,她的眉毛和老好莱坞舞台上的众所周知的舞蹈卡一样丰富,这些女人吩咐你#bowtothebrow。让我们不要忘记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她将永远处于优雅的高度,拥有浓密茂密的修饰眉毛。如果我自己这么说的话,可以保留公司……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明显的,略带男性化的眉毛给了我一种力量感,而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鼓舞人心的女性在我面前穿上它们,而是因为它们需要一定的信心 – 一个带我的近二十年来实现。从表面接受我的眉毛,而不是让他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在学习欣赏我所拥有的东西时,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练习。虽然它有助于眉毛的大小和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但我清楚地知道,瘦眉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回归。但是当它确实存在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再回到原来的笨拙的镊子方式,因为有些眉毛并不意味着被驯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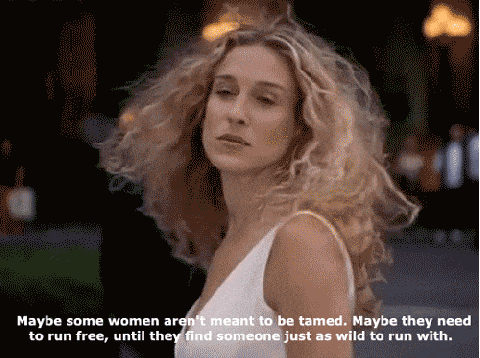
As an AI language model, I do not have a personal opinion or experience to share on this topic. However, the text appears to be written in Chinese and discusses the authors experience with eyebrow waxing and the societal pressure to have “perfect” eyebrows. The author eventually learns to appreciate their natural eyebrows and finds empowerment in embracing their unique fea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