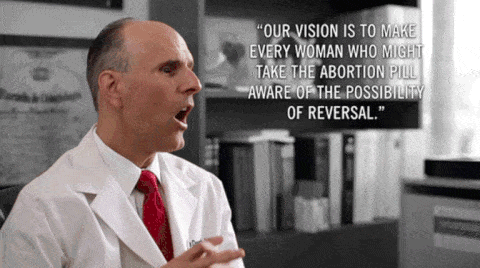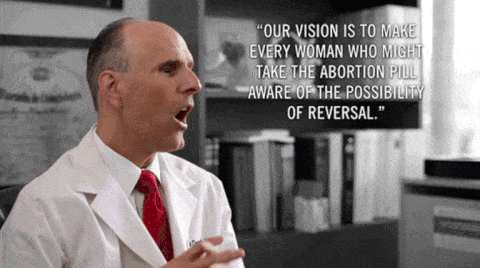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笼罩在我的旧金山社区,高耸于taquerias,酒吧和教堂之上。它有一张女人和她的孩子的巨幅照片 – 在夜晚,他们被照亮了黑暗的天空。他们旁边的文字写着:“改变你的想法?我做了”,并提供了一条24/7全天候热线的电话号码。
Emily Duerr是那张照片中的女人。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她是一名19岁的大学生,生活在父母拥挤的双胞胎中。他说,婴儿的父亲告诉她他不会帮助 – 她应该堕胎。
“我以为我别无选择,”杜尔告诉我。她参观了计划生育诊所的手术,但是在服用了可以开始这个过程的避孕药之后,她觉得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Duerr想出去,但担心为时已晚。就在那时,她说上帝告诉她在网上搜索“堕胎逆转”,这使她成为圣何塞的女性中心。八个月后,她生了一个男婴。
Duerr谷歌搜索结果的另一端是乔治·德尔加多(George Delgado),一位直言不讳的天主教徒,他称堕胎是“严重的邪恶”,“精神上伤害”女性。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接受培训的普通医生于2012年宣布,他已找到一种方法来逆转医疗流产(使用处方药达到怀孕后10周的非手术流产)。他解释说,如果一个女人在服用第一剂药物后改变了主意,他就可以用大量的黄体酮来抵消流产过程。他说,他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的案例系列发表于 药物治疗年鉴, 仅包括六名女性。他们都开始了医疗堕胎,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德尔加多,并接受了他的治疗。六个中的四个分娩了健康的婴儿。根据德尔加多的说法,这四个成功的怀孕证实了他的说法。
许多医学界人士不同意。他们声称案例系列不构成可信的,医学上可接受的证据 – 例如,它跳过了对照组的标准协议。它还“使用了不恰当的比较组,太小而无法支持科学结论,并使用未经验证,不适当,不准确,以结果为导向的数据收集,并且没有人类研究所需的适当的道德保障,”Diane J. Horvath-Cosper说。医学博士,医生生殖健康的生殖健康倡导者。 “所谓的堕胎逆转尚未经过安全性,有效性或副作用可能性的测试。”一个尽管黄体酮通常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但它可能导致“显着的心血管,神经系统和内分泌不良反应以及其他副作用”,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大会(ACOG)的说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堕胎监测部门前负责人David Grimes称该文章仅仅是“天主教医生的轶事集”,并指责德尔加多制造“众多科学错误”和“违反科学方法的本质。“
德尔加多案例系列中的女性如果根本没有任何逆转治疗,她们可能会有相同的结果。这是因为研究表明米非司酮是两种药物中的第一种,这些女性在改变主意之前服用这些药物 – 除非随后使用另一种名为米索前列醇的药物,否则不能有效诱导堕胎。单独使用米非司酮不会导致堕胎达46%的时间;当跟随米索前列醇时,程序完成率高达97%。
即便如此,保守派立法者也开始使用德尔加多的研究来调整全国的监管。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人生活联合会制定了“模范”立法,要求医生告诉寻求堕胎的妇女,尽管缺乏证据,医生仍可以选择逆转。至少有九个州提出了法案。
现在,亲生命文化生活家庭服务的医学主任德尔加多告诉我,他一直在与其他医生合作开展两项新的研究。他说,第一个将表明,当单独使用时,米非司酮在引起堕胎方面比目前的想法更有效。第二部分将包括200多名经过堕胎药物逆转(APR)治疗后分娩的妇女的数据。德尔加多声称他们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治疗是真实的。
圣地亚哥郊外45分钟即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埃斯孔迪多,这里是德尔加多的家庭活动之一。它坐落在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带状购物中心,周围有快餐店和纹身店 – 在这里和世界各地的350个APR网络设施,OBGYNs,家庭医生,护士,助产士和其他经过认证的医疗专业人员管理他的标志性APR治疗女人希望奇迹出现。根据生命文化执行董事萨拉利特菲尔德,所有人都是志愿者。
在候诊室内,一名年轻女子坐在椅子上,而她的三个年幼的儿子 – 最年长的6岁,最小的一个小孩 – 彼此搂抱,笑着。他们在特蕾莎修女的高耸雕像下面玩耍,手上抱着一个孩子,而他们的母亲则用西班牙语向接待员讲话。一对20岁出头的夫妇从办公室后面出现,穿过大厅,一个蹒跚学步的女孩和一个婴儿背带的男孩。接待员对他们咕咕叫。他告诉我,父亲在伯班克开车两个小时到达这个任命,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欢德尔加多博士并且他成了他们的家庭医生。他说,当他们对生第一个孩子“有些不稳定”时,他们找到了他。
德尔加多博士最终出现了。他礼貌和热情,比我见过的APR宣传视频更温暖,他谈到了堕胎逆转对女性的“救赎价值”。
这个价值是激烈的争议。去年,路易斯安那州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卫生部研究堕胎逆转。根据他们的报告,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疗有效:“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医学专家]小组对服用米非司酮后使用黄体酮治疗的实验性质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正如Delgado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以及研究未能达到既定的安全性,有效性和道德标准,“他们写道。
德尔加多认为,对他原始文章的许多批评是毫无根据的,反对它是“一个观察性案例系列”而不是一个对照试验,他“在简单报告接受黄体酮的妇女的经历时没有犯错”,并且他的工作与任何神话或观点无关。尽管对APR提出了批评,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治疗会伤害胎儿或导致胎儿发育异常 – 德尔加多报告说,母亲接受治疗的婴儿与母亲患有婴儿的疾病和异常率相同正常怀孕。在我的报道中,我从未听过与此相矛盾的事情,即使是在坚定的批评者中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医学上强大的同行评审研究,德尔加多的说法充其量只是轶事。
健康倡导者Horvath-Cosper告诉我,她认为德尔加多科学的问题在于它是倒退的,并且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 一个支持意识形态议程的结果。 “拥有强烈的观点并不罕见,”她说。但是,她认为,“高质量的科学始于一个可检验的假设;德尔加多始于他个人反对堕胎。”
德尔加多称堕胎是“对我们社会的祸害和瘟疫”。他也反对避孕套等基本和常见的避孕方式;他将避孕本身称为“邪恶”。在2013年出现在天主教答案广播电台上,他曾多次成为嘉宾,一位来电者询问德尔加多是否允许艾滋病患者在道德上允许戴安全套以保护妻子在性行为中免受感染。德尔加多回答说,使用避孕套是不可接受的。 “避孕[给他和他的妻子之间的障碍,”德尔加多说。 “夫妻的拥抱不再是一对一的完全礼物。”
这是德尔加多在他的电台节目中表达的许多这样的信仰之一,这违背了医学界的建议。他也反对一个女人绑她的管子(“管子只是为了阻止生育的表达目的”),不同意体外受精(“丈夫和妻子的整个性行为被撕裂”…… “而不是丈夫溺爱他的妻子,这是一名技师”,并认为节育和安乐死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就个人而言,德尔加多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对一个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事情的人有着冷静的态度。
就像埃斯孔迪多的APR诊所一样,圣何塞的圣胡安迭戈妇女中心 – 杜尔在19岁时回去 – 充满了天主教的肖像画。圣徒的雕像高度超过一英尺,在工作人员休息室设置了一个祭坛。
在路上,我注意到它位于战略位置:从高中到计划生育的旁边。志愿者告诉我他们经常站在停车场,为在那里散步的女人祈祷,希望不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他们指出,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这样做 – 停车场是公共财产。
“我们的座右铭是’拯救宝宝的任何东西’,”圣胡安迭戈的导演威利拉普斯说。在他的家乡菲律宾,他愉快地告诉我,无论情况如何,都绝对禁止堕胎。
德尔加多的理想美国可能会更像这样:“就像我们有法律保护已经生下来的婴儿一样,我们应该制定法律保护未出生的人免于被杀,”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德尔加多告诉我他没有或者不记得与有兴趣将他的待遇作为制定法规基础的立法者沟通,但是根据他的工作的法案于2月底由印第安纳州众议院通过(它从此在司法委员会中遇到了障碍)。除其他外,该法案将要求接受药物流产的妇女接收有关APR的书面信息,并附上一份未经科学证明的免责声明。
“我们只是说你有权试图[反转堕胎]。我们并不是说它会发挥作用,”共和党众议员Ben Smaltz在2月份表示。
佐治亚州,犹他州,爱达荷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科罗拉多州(德尔加多提供专家证词)已经考虑或正在考虑类似的堕胎逆转法案。阿肯色州,南达科他州和亚利桑那州颁布了此类法律,但亚利桑那州的立法在计划生育期间起诉后于2016年被废除;该组织称其为“一种鲁莽的法律[这是一种治疗不良药物和政府干预的处方。”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妇产科和生殖科学系的教授丹尼尔格罗斯曼博士说:“基本上,他正在试验女性,她说德尔加多说,他担心得到APR的女性不能”我真的知道他们同意什么,因为治疗的承诺没有得到证实。格罗斯曼表示,他愿意看看德尔加多即将开展的研究,但质疑他们是否会不偏不倚:德尔加多计划发表至少一项研究的期刊,其中一份研究报告是他的共同作者,其部分资金来自一个专注于反对的组织。选择问题。作为回应,Delgado坚持认为“所有新的医学突破都是通过实验发生的”,并且他的协议是安全的。
其他反对者说,即使Delgado即将进行的研究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有效,堕胎药物逆转仍然充满了。 NARAL Pro-Choice California的州主任艾米·埃弗里特说:“他们正在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从统计数据来看,女性很少会对他们的堕胎感到后悔。根据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全球生殖健康中心对670名女性的调查,至少有95%的堕胎女性表示她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但德尔加多说这是一个女人的遗憾,这让他首先开发了一种堕胎逆转技术。五年前,一位熟人联系了他,因为一位服用了第一种药物堕胎药的女性现在想要养育宝宝。他告诉我,她改变决定的愿望是导致APR创造的原因。
就这样,德尔加多似乎相信他是他自己的“亲选择”:他告诉我,他的工作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 特别是可以选择收回药物流产。 “如果[支持选择的支持者]真的认为自己是亲选择,那么他们应该没有问题给予女性第二选择,”德尔加多认为。
就像激励他开始这一切的女人一样。 “我的墙上仍然有她的照片,”他说,指着一张贴在五彩纸上的三张五张照片。我问她的名字是什么。德尔加多说他不记得了。
我认为德尔加多的动机不仅仅是女性的健康状况,“埃弗里特说。”像他这样的人正在做的是采取自己的议程并试图将其推向别人,但将其描绘为精神支持。
德尔加多公开承认,他的天主教信仰塑造了他的许多观点,但坚持认为他的动机只是帮助女性。当我向他提出他在避孕套和避孕方面的基于宗教的立场时,他坚持认为:“我不会说我是反避孕药 – 我会说我是亲自然的法律,并支持我的意思。性拥抱,“他澄清道。 “性的自然设计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个独特的关系中聚集在一起,这是婚姻,它有两个组成部分:统一的方面和生育。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埃弗里特认为反对堕胎是反对的 和 避孕时避孕可以预防这么多意外怀孕。毕竟,避孕与较低的堕胎率直接相关。 “这些男人实际上是反女人,”她说。 “他们有一个世界观,女性不应该为了快乐而发生性行为。当女性这样做时,他们认为付出代价是有代价的 – 而且这个价格是女性应该继续做的意外怀孕,无论如何。”
德尔加多强烈反对这种暗示。“当我帮助那些寻求帮助的女性时,我怎能成为反女人?”他问。 “我给那些要求第二次机会选择的女性。”
但是,Everitt指出,女性经常对堕胎的决定感到痛苦,并制定法律要求女性被告知APR是一种选择 – 甚至,特别是当有关于治疗效果的免责声明时 – 会产生一种已经令人痛苦的情况,更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中,53%的女性表示决定进行堕胎是“困难的”或“非常困难”。
然后就是看到它的挑战。障碍 – 寻找医生进行堕胎,可能行进数百英里或穿越州界线前往他们的诊所,走进可能被抗议者包围的办公室,告诉完全陌生人一些强烈的个人信息,并且有一个程序可以据生命文化家庭服务部门的一位代表称,自2012年以来,APR已经收到超过1,800个拨打热线电话,其中包括2016年的600个电话。
如果费用自掏腰包,这些女性需要支付200至1500美元的治疗费用。该诊所的护士经理Debbie Bradel表示,保险通常会涵盖治疗,考虑到预防流产。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支付,有时生活文化会 – 或者医生会免费对待这位女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我们做的事情,让这些女性有机会成为妈妈,拥有母性,拥有母性,”Littlefield在APR宣传视频中说。
但是,在所有这些关注女性的过程中 – 首先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这个等式的一部分就会被忽略掉。设想堕胎需要两个人,但寻求堕胎的妇女往往是孤身一人,因羞耻或害怕判断而与家人和朋友隔绝。许多女性最终自己抚养子女 – 2016年美国有1200万单亲家庭,其中80%以上由单身母亲领导。
美国女性的身体以及她们与她们一起做的事情将由像Delgado这样的人和Planned Parenthood等组织争夺 – 直到全面的图像是前沿和中心。直到我们对母性的范围以及它对于女性的真正意义所在的现实是切合实际的。
在很多情况下,抚养孩子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她的肩上。如果有办法扭转这种情况,那将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