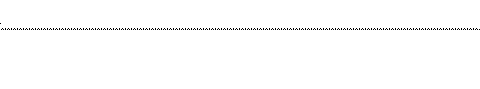盒子说你必须等两分钟,但它就在那里。在我与六个女朋友分享的大学房子的蓬乱卫生间里,我从我的大腿之间拉出湿棒。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清楚白天是粉红色的加号,这证实了我怀疑这次我已经搞砸了。
我瘫倒在沙发上,而我的一次又一次的伙伴盯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坚持了这个测试,所以他可以亲眼看到我一直在抱怨的疲惫和烦躁不仅仅是延长宿醉的症状。在我手中是卑鄙的事实:我喝醉了。我是不负责任的。而现在,我怀孕了。
“它已经说得很积极,”我抽泣着,因为不能再否认它而感到苦恼。只是片刻,我让它的恐惧和巨大抓住了我。我没有克制或义务地哭了。当我抬头看时,应该握着我的手的人正站在门廊上,抽着烟。
在最初的启示和随后的哭泣之后,我开始行动起来。一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我家乡的计划生育,距离我们45分钟路程,结结巴巴地说:
“嗨,嗯,我怀孕了,我……我需要预约。”
“你打算安排进行产前检查吗?”
“没有。我打算安排堕胎。“
接待员问了我几个问题,并给了我下一周最早的预约。我想象你可以随时,一周中的任何一天进行堕胎。但令我震惊和沮丧的是,我将不得不再怀孕7天。关于保持那种方式我有点惊慌失措。虽然我最好的朋友都知道,但我觉得我只是通过身体存在就告诉世界其他地方一个巨大的谎言。
与此同时,我放弃了悲伤。毕竟,为什么我要悲伤?毫无疑问,我立即知道了我必须做的事情,并与我的准男友分享了我的计划。他所拥有的任何感情都是沉默和短暂的 – 他首先忘记了他从未想知道的事情。当我告诉他我将要堕胎时,他显然松了一口气。我不介意他的透明度。但他没有问我的感受,不是一刻,一周或一个月后。他从来没有提起过。
我对终止妊娠的任何感觉似乎毫无意义且不受欢迎。我不会为不会再次出现的婴儿流下眼泪,至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不会。相反,我把它推到一个我确定无法找到的地方。
有一个星期我走路上课时吃了一顿,呛了一顿饭,藏在我的房间里,远离聚会,酒和香烟。如果我抽烟或喝酒被遗忘无关紧要,但我不想这样做。我病得太厉害,不能喝威士忌。即使是我室友烧焦的烤面包的可怕气味也让我冲向浴室。但独自一人感觉更好,在那里我可以确定我既不是哀悼也不是庆祝。除了感到极度恶心并期待不再生病之外,我等待着我的任命。然后在星期三早上,我焦急地回到巴尔的摩进行手术。
我在候诊室里烦躁不安,妈妈静静地坐在我旁边。最后,我听到了我的名字,最后一位病人 – 当天最后一位被释放的女性。手术很短,但比我预期的更痛苦。我发出尖锐的,意想不到的尖叫声,助手从我的大腿上擦了一下血迹。之后,我母亲开车送我回家喂我fajitas,我吃得很贪吃 – 我的病已经消失了。那天晚上,当我爬进我儿时的床上时,我打电话给我的非宝宝的非父亲,但他没有接受。后来我发现,当我在巴尔的摩的家中流产了他创造的一半的胎儿时,他已经和他的前任一起回到了晚上。感觉就像是在庆祝。
我早上开车回学校。我情绪和身体恢复正常。我做出了我认为可以信任的唯一选择,而且我非常感激我的能力。生孩子会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我上大学,几乎没有通过我的课程,像鱼一样喝酒。我会在未来几年内滥用酒精而苦苦挣扎,但在我生命中的这一点上,我不确定母性是否已足以让我摆脱困境。事实上,它可能会让我陷入更深的境地。我的堕胎也标志着我不想再陷入不稳定关系的结束了。缺乏成熟或支持使我意识到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前任。
我的选择并不容易,但我确信这一点。所以我不会感到内疚。我不会悲伤。我一直是一位优秀的女权主义者,并且相信女性有权进行安全合法的堕胎。我只是利用自己的生殖权利,就像我认识的许多女性一样。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可以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佳决定。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几乎没有想到它,至少没有任何悔恨或情绪。
几年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合伙人。而且因为我还是醉酒,或者因为节育从未与我达成过一致,或者因为我家里的所有女性都非常肥沃,所以有一次我们怀有无保护的性行为。简而言之,我认为没有孩子。但我年纪大了,不在学校。我是一个忠诚的关系。我们(通常)按时支付租金。它仍然不理想 – 钱很紧,24岁时我没有准备好生孩子。我周围没有其他人怀孕了,而且我没有感受到一些女性在开始故意生育时的感觉。但我确实有一点希望,我可以处理一个婴儿和随之而来的一切。
现在,在32岁的时候,我有两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像飓风一样进入了我的生活 – 从他们出生后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无休止地呕吐到不睡觉 – 他们让我失望并重新塑造我超过1000次,我相信他们会一次又一次。我已经做了七年的母亲。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挑战。
大多数情况下,母性的硬度让我意识到我的堕胎并非徒劳。十年前,我没有勇气成为一名父母,尤其是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我认为这会毁了我,因为即使在我最好的一天,作为一个母亲,有时也会毁了我。即使我想这样做,它也是不可阻挡的,势不可挡的。
不过,近年来,我已经想过“如果会怎样?”当我第一次感觉到女儿在我体内踢的时候,我把手放在肚子上,感觉到了她的力量。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如果我什么也没做,我会在几年前感受到这些踢。我现在的朋友和孩子比我年轻几岁。有时我发现自己正在看着自己的儿女,理解我没有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年龄。
在这些时候,我已经走下了想象我几乎是孩子的兔子洞,我很伤心。悲伤无处不在,让我胸部受伤。有时我会在淋浴时哭泣,我的心痛得知道,如果我选择的方式不同,世界上会有另一个人。那时我几乎没有停下来考虑它。我没想到会有另一种选择,因为对我而言,它并不像真的那样。那时我的思绪已经弥补了,但我现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是一个母亲,所以我的心痛只有母亲的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没有权利承认这些感受。我一开始就快速而有目的地继续前进,因为感受那些黑暗的感觉没有任何意义。此外,这不是流产或悲剧 – 这是一个选择。但这是一个没有关于如何感受的规则书。
做母亲让我更加感激,我必须选择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合法堕胎的权利至关重要,因为妇女总是需要这种选择,无论是否合法。历史告诉我们,当女性无法获得堕胎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儿童出生在严峻的形势,寄养家庭变得拥挤不堪的儿童,家庭生活在贫困中,妇女死在小巷或无牌医生的桌子上。
尽管如此,相信安全,合法获得堕胎是妇女的权利是一回事。个人决定拥有一个是另一个。因为我们迫使人们落在政治光谱的一边 – 我们要么是支持选择,要么是反选择 – 堕胎行为有时被视为明确。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总是。
据统计,只有极少数女性对堕胎感到遗憾。我并不完全后悔。这是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做出的决定,而我现在意识到的选择将留在我身边。
我花了很多年才承认,甚至对我自己来说,我的堕胎并不像我想要的那么简单。但也许它不一定非常简单。作为一个优秀的女权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一个相信选择的女性,并不意味着我对我所做出的选择仍然不会有复杂的感受。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感觉,或不感觉,或继续。